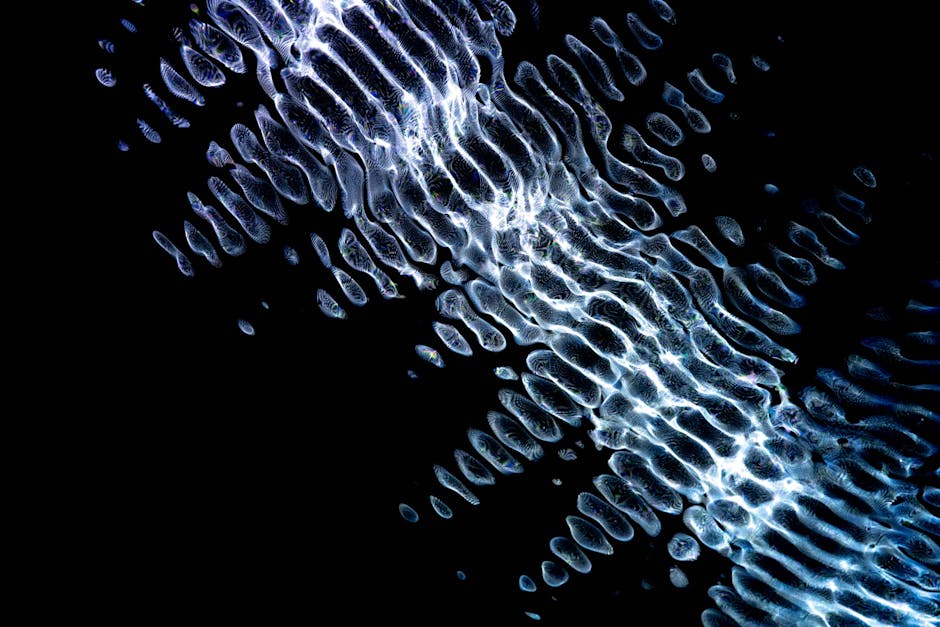在玛格丽特·米切尔的宏篇巨著《飘》中,白瑞德船长远不止是一个精明不羁的商人,更是一位洞察世事的“人间清醒者”。在亚特兰大那场为伤兵筹款的银币音乐会上,当众人还沉浸在南方邦联的爱国热情中时,他却发表了一段惊世骇俗的言论,如同一把冰冷的手术刀,剖开了战争温情脉脉的“神圣”面纱。
“凡是战争都是神圣的,”他说,“对不得不去打仗的人说来就是如此,试问发动战争的人如若不把它说得那么神圣,还有哪个傻子会去打仗呢?然而不管演说家们怎样对去打仗的傻瓜鼓吹战争,也不论他们把战争的目的说得多么高尚,打仗的目的只有一个,那就是为了钱。一切战争实质上都是为了争夺金钱。可惜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几乎没有。大多数人的耳朵里充斥着军号战鼓声,以及平平安安坐在家里的演说家的美妙言词。他们鼓吹战争的口号因时而异,时而大喊‘从异教徒手中抢救基督之墓’,时而狂叫‘打倒教皇!’时而高呼‘棉花,奴隶制和州权!’”
这段发言以冷峻的讽刺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:“神圣”是动员“傻子”们走上战场的必要工具。当权者需要用崇高的理想、民族的存亡或上帝的旨意来包装战争,才能让普通人甘愿为之牺牲。这种“神圣感”是战争的麻醉剂,它让士兵们暂时忘却对死亡的恐惧,并在精神上获得一种殉道者的荣耀。
白瑞德将战争从意识形态的云端拉回到经济利益的地面。无论口号多么响亮,旗帜多么鲜艳,驱动战争最根本的动力,始终是对资源、财富和商业控制权的争夺。
三个跨越时空的战争口号,完美地展示了历史如何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样的剧本:“从异教徒手中抢救基督之墓”指的是十字军东征,表面上是基督教世界“解放圣地”的宗教使命,实则是欧洲封建贵族、商人与教会争夺贸易通道、土地和财富的掠夺运动;“打倒教皇!”则直指宗教改革与宗教战争1,新教诸侯与天主教势力的冲突,背后是教会财产的再分配、王权的巩固与商业资产阶级的崛起;“棉花、奴隶制和州权!”则是美国内战中南方精英的遮羞布,所谓“州权”维护的,是奴隶制这一经济基石,而“棉花”更是赤裸裸的资本利益。三个口号,跨越数百年,却共同暴露了战争的永恒真相:权力者以意识形态或道德名义煽动民众,而真正的驱动力,始终是金钱、资源与统治权。
白瑞德的言论,不仅是对战争的解构,更是对人性中“被蒙蔽”与“被利用”的冷静揭示。
为什么这个简单的道理,懂得的人却寥寥无几?军号战鼓激发着热血,演说家的慷慨陈词塑造着正义。人们往往更愿意相信一个崇高的理由,而不是接受一个冰冷的利益算计。这种情感上的共鸣与认同,使得我们极易被煽动,从而忽略了去追问“谁才是这场战争真正的受益者”。
重读白瑞德的这段话,在今天依然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。它提醒我们,在面对任何被冠以“神圣”之名的宏大叙事时,都应保持一份冷静的审视和独立的思考。
我们需要听见军号与演说,但更要有勇气去探究那背后的沉默真相。白瑞德的智慧,在于他穿越了时代的迷雾,直抵了人性的弱点与权力的逻辑。这或许正是《飘》历经近百年,依旧魅力不减的原因——它不仅在讲述一个关于爱情与生存的故事,更在探讨关于社会、人性与历史的永恒真相。